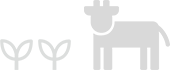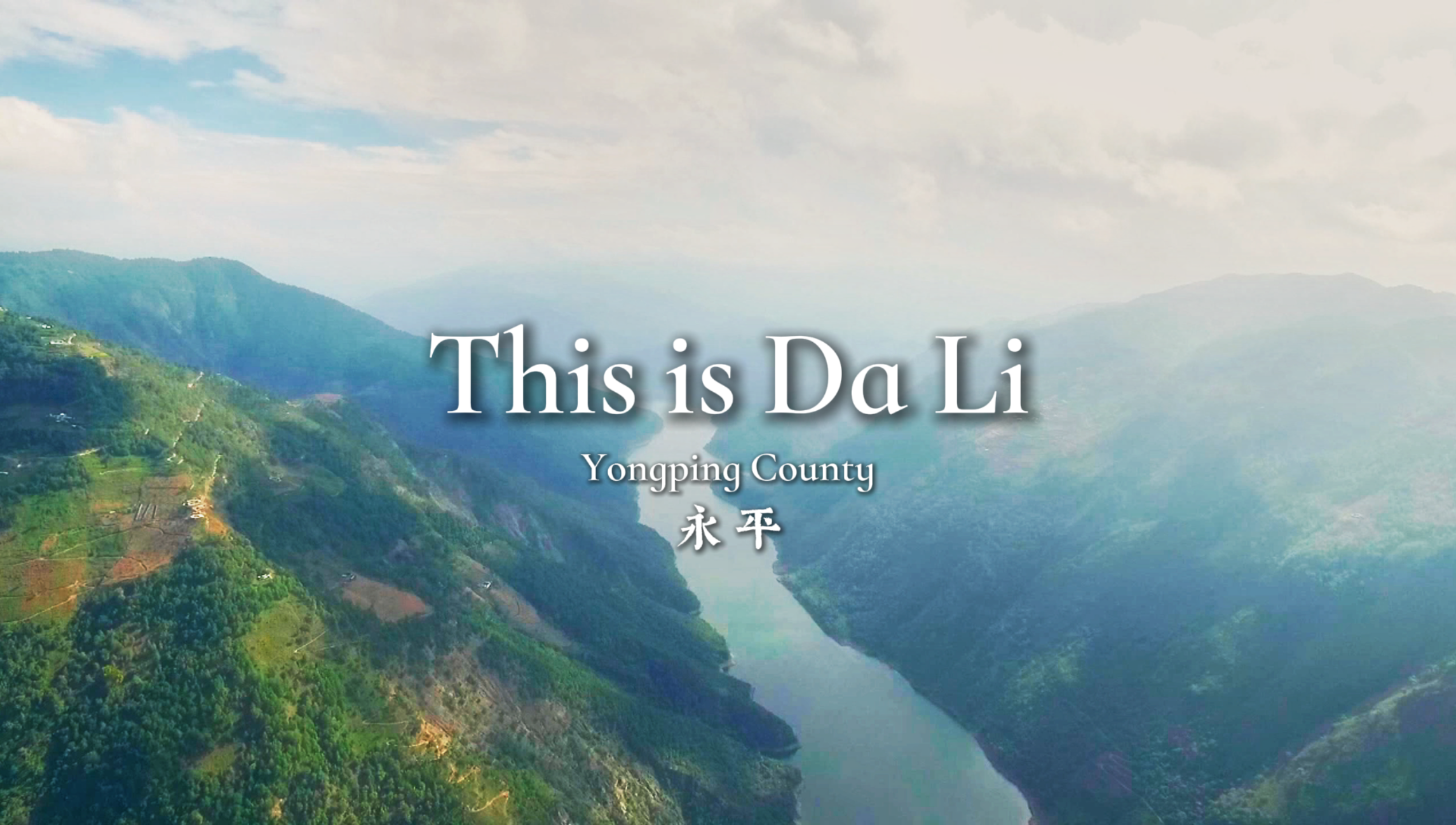文:李灿斌
图:洱源发布
视频:云南乡愁
"记得有空再回来闲嘎,你爸爸和我一起长大呢。这是我们自己家做呢,带上尝尝!"端午节时,儿子从昆明回来,我们一家回到老家小住,离开家乡返城时,儿时的伙伴明明追出来,给我儿塞上一小捆乳黄色的乳扇,一定要让带上。再三推辞未果,我只好让儿子接过,放到后排车座位上。汽车缓缓离开家乡,迎面扑入眼帘的是路旁青青的树木和一望无际的的田野,带着泥土和青草味的空气夹杂着乳扇浓浓的奶香弥漫在整个车厢里。

家乡洱源县邓川镇位于大理坝子北端,水源丰富,良田万顷,有著名的高原湖泊绿玉池、西湖、东湖。辖区内永安江、罗时江、弥直河从北向南而过,从空中鸟瞰,像一个隶书体的“川”字写在坝子里。优越的自然环境,把家乡造就成著名的高原鱼米之乡;山清水秀,气候温和,水草丰茂,为家乡大量养殖乳牛奠定了条件。有一句话这样说:"食百草,所以奶汁特别好。"邓川的白族人,对奶牛饲养是非常用心的,除了在家精心喂养外,记得小时候,每天割草、放牛成为许多孩子放学后的必修课。那时家乡放养奶牛的方式很特别,奶牛专门由一个人牵着,穿梭于庄稼地之间碧绿的田埂上,既要把牛放养好,又要不让牛偷吃庄稼。于是,蓝天白云下,阡陌纵横的田野里,牛吃草的声音、悠扬的短笛、稚嫩的牧歌成为我们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。

渐渐地,随着时光的流逝,我们渐渐长大,放牛的事由弟妹去做了。放学后,我们也加入了到外地割草的行列,骑着自行车,列队和青年人一道去外地割草,在当时看来,是一种多么"酷"的感觉。朦胧的月光下,我们带着装满青草和星光的竹筐,在清脆的铃声中,驶向"家"的方向,心里充满着朦胧的成就感。记得那次去东山上割草,我和明明一边骑车一边聊天,聊到高兴处,哼起小曲,吹起口哨,竟然到割草的地方还浑然不知,多骑出去了2公里。明明大我一岁,我习惯喊他“明哥”,我遇到什么他都主动来帮助我,比如帮我捆草垛,有时他割好草后,还会来帮我割。他说,他想去当兵,每次经过炮团驻地,我们都要驻足向里面好奇地遥望很长很长时间。在我上高二那年冬天,带着我无限的牵挂和祝福,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,奔赴雪域高原西藏,在后来的三年时间里,由于表现突出,还立了三等功。明哥去了军营,也带走了我有关骑自行车割草的趣事,这份牵挂一直延续到高中毕业,延续到我后来读书的省城。至今,那些日子依然是我对青年时代、对故乡最珍贵的记忆。这次回家,明哥还拿出我们当年往来的书信给我看。皱巴巴的信纸,稚嫩但依然清晰的字迹,如同曾经坎坷的岁月和稚嫩的我们,不知不觉中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眶。

由于盛产鲜牛奶,家乡人发挥聪明才智,把鲜牛奶发酵、加热,用竹筷将乳汁摊成薄片铺在竹架上晾干,变成了"形似扇、薄如纸",黄中带白、醇香甜美的乳扇。这就是云南十八怪中——牛奶做成扇子卖,邓川乳扇由此而得名。用火煎炸后,撒上些许白糖,香酥可口。家乡邓川的白族女子,大都擅长做乳扇。我的母亲、姐妹都是做乳扇的高手,由于发酵和加热的火候温度掌握得好,她们做的乳扇外形美观,厚薄均匀,清香而富于口感。

今夜,当我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写这篇文章时,沥沥淅淅的雨打在窗户上,绽放成一朵朵美丽的鲜花。鲜花伴着美妙的音符,展示着大自然创造的转瞬即逝的美。故乡的山,故乡的水,故乡的亲人,以及儿时的朋友……清晰地向我涌来,他们一定在雨中品味到丝丝甘霖的欣喜。淡淡的路灯下,我仿佛回到故乡,在风调雨顺的高原水乡,我又仿佛闻到故乡浓浓的奶香了。